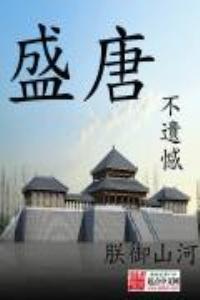一個青樓記女,就如水中的浮萍,官紳名士們捧你時,可以把你捧成蟾宮之桂,高不可攀,若想整治你時,地位還不及一個升斗小民,不過就一賤民而已。而就是這樣一個女子,竟敢以酒潑向這麼多的官員也得窺其顏色、仰其鼻息的國公爺,一時間滿堂皆驚!
夏潯的反應很快,習絲姑娘的手腕一動,他就察覺有異了,但他非常鎮定地坐在那兒,一動也沒動,他只是很迅速地閉上了眼睛,於是……,一滴酒也沒濺到眼睛裏。
酒液潑在夏潯臉上,順着他的臉頰緩緩淌了下來,整個宴客廳里,所有人全呆住了,官員士紳們自然不消說了,就連那些端酒侍菜的奴婢下人們都呆住了,兩廂里的樂師們抻長了脖子拼命地往外看,其中有個拉琴的老者方才只顧低頭,沉醉在自己的樂曲聲中了,根本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,這時急得他跟什麼似的,一個勁地扯着旁邊那人小聲問:「夥計,咋了,夥計,到底咋了?」
常知府的臉當時就青了,他挺着一張青滲滲的臉,強忍了忍才沒有跳起來,只是「啪」地一拍桌子,獰笑道:「習絲姑娘,你敢胡言亂語詆毀朝廷命官!又酒潑國公,以下犯上,不知王法麼?」
習絲姑娘鄙夷地瞟了他一眼,高傲地昂起了頭,曬然道:「知府大人如此氣極敗壞,那吃人的人,莫非就是你麼?」
常英林狼狽不堪,又氣又急地吼道:「大膽刁民,妖言惑眾,誹謗朝廷命官!來人吶,把她給我拖出去!拖出去,把她……」
穩穩噹噹地坐在那兒的夏潯從袖中摸出一方手帕,溫文爾雅地擦了擦臉頰,就好象剛剛淨過面洗過臉似的,他擦完了臉,這邊常知府也剛下完了令,夏潯慢條斯理地道:「府台大人何必着急呢,防民之口,甚於防川!若不叫她一吐衷腸,倒像是湖州府真的做了什麼天怒人怨的事兒,傳揚出去,殊為不美!」
一旁俞御使一直在緊盯着夏潯的反應,一聽他這樣的語氣,立即洞燭於心。要做官,要做個成功的官,沒有這點眼力哪成,不說他們個個都是人精吧,揣摩上意這方面,也是都擅長的。俞御使立即咳嗽一聲,正氣凜然地道:「本官都察院御使俞士吉,奉旨巡視災區,專查不平之事,習絲姑娘,你有冤屈,可向本官申明,但是本官醜話說在頭裏,以民告官,若舉告不實,可是要罪加一等的!」
「告官?我沒有告官!」
習絲姑娘的一句話,使得滿堂又是一愣,你不告官,卻說這麼一番話,還酒潑國公,發了失心瘋麼?
習絲仰起臉兒來,那臉蛋膚色如玉,嫩如蛋清,被燈光一照,映得如同透明,煞是惹人喜愛,可她的眸光里卻隱隱地泛着淚光:「小女子既不是苦主,也不曾蒙冤,湖州大水,無數人破家,可習絲照樣錦衣玉食、出入豪門,笙歌燕舞,夢死醉生,有何冤屈可言啊?」
她忽低下頭來,冷銳的目光在夏潯等朝廷大員們臉上一掃,咬着牙道:「習絲只因那所見所聞,胸中有不平之氣,不鳴難安!」
夏潯仿佛方才潑的是別人一般,泰然自若地笑道:「好!不平則鳴,相信對俞御使來說,這是比輕歌曼舞更加中聽的。」
習絲姑娘見慣了貪官污吏的嘴臉,心姓自然有些偏激,再加上先前常知府所散播的他與輔國公府有交情的傳言,先入為主之下,已然認準了夏潯是個貪官,這時聽他口口聲聲不忘拉住俞御使,把問責之事都推給他,更認為他是預留退路,方便包庇常知府,心中更是恨極。
她冷冷地瞟了夏潯一眼,說道:「習絲祖上,世代務農,原也是良善人家。十一年前,這裏也發過一場大水,因那一場大水,我的家……沒了!那一年我才七歲,我是被我爹噙着淚賣進青樓的,可我不恨他,他也是沒法子……」
習絲姑娘說到這兒,兩行清淚撲簌簌地流下來,哽咽着道:「「那狗官為了政績考評不致影響自己的前程,先是對災情匿而不報,繼而橫徵暴斂,務求照常完成當年的秋賦徵收,天災不曾害死那麼多人,可這人為的禍呀……,我的父母家人熬過了洪水大劫,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