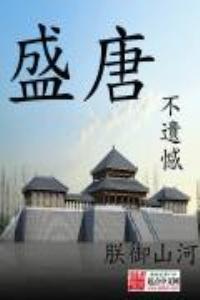出敦煌,西南是陽關,西北是玉門關。
黃河遠上白雲間,一片孤城萬仞山。
羌笛何須怨楊柳,春風不度玉門關。
春風自然是能吹過玉門關的,可是此時的玉門關外卻只有皚皚白雪和呼嘯的寒風。
好在,春天將近,寒風凜冽的時候少了,大部分時間風是比較輕柔的,於是遠山銀雪、藍天白雲,給人的就只有空曠浩渺的感覺了。
夏潯已離開敦煌,啟程趕往哈密。
哈密的情況同敦煌不同,而且哈密有自己的王,對哈密他無法像對敦煌一樣採取相同的手段。不過,哈密還是有必要去一趟的,一時的得失可以不計較,民心的向背卻必須得計較,早早做些準備,一旦哈密失陷,將來收復後也容易治理。
今天的天有點陰,雲不是很白,天卻依舊是那麼藍,遠山陷於一片霧靄之中。
大旗曼卷,馬隊行走在這浩渺無垠的大地上,作為唯一活動的群體,給這蒼涼悲壯的大漠戈壁增添了一分活力。
不知什麼時候,隊伍中有人扯起喉嚨唱起了高亢嘹亮的西涼民歌:「大姐姐給了一個木匠家,又會蓋樓又會砸椽花,楊柳葉兒青呀,又會蓋樓又會砸椽花,二姐姐給了個鐵匠家,又會打鐵又會拉風匣,楊柳葉兒青呀,又會打鐵又會拉風匣……」
嘹亮悠揚的歌聲讓這高天大地間行進的隊伍有了幾分生氣,夏潯也凝神傾聽着,當那聲音停歇,他喟然一嘆,回首看着伴在左右的劉玉珏和陳東、葉安,說道:「若不是我,你們也不會跑到這天邊兒上來,很辛苦吧?」
陳東葉安騎在馬上,神采飛揚:「國公,這樣的天地,若在金陵城裏,哪能得見,我們喜歡的很呢。」
劉玉珏則凝視了夏潯一眼,說道:「快活地過,是一輩子;悲傷地過,也是一輩子。順境逆境,有時由不得咱們自己,知己長伴,何嘗不是快樂?」
「好兄弟!」
夏潯的大手重重地拍在劉玉珏的肩上,扭頭便對坐在車前,興致勃勃地看着那亘古不變的蒼涼風光的西琳和讓娜道:「來,莫讓軍中弟兄專美與你前,你們是龜茲古國的人,最擅長的就是音樂,也唱兩首曲子來,叫大家提提精神!」
出了玉門關後,卻往西來,西琳和讓娜越興奮,現在天氣已經不那麼寒冷了,很多時候,她們都跑出車子,坐在外面,興致勃勃地看着那天那雲、那山那樹,仿佛出了籠的小鳥兒般快活。對故鄉,不管那裏留給你的回憶是悲傷還是喜悅,想起來時總是有種沉甸甸的感情的。
西琳含情脈脈地看了夏潯一眼,扶着那車棚站穩了身子,忽然振聲唱了起來:「當戀人在果園裏撒歡,我的旋木雀會縱情歌唱。當夜不能寐把你思念,我渾身的愛火燒得更旺。百靈鳥會不會啼鳴翱翔,心上人會不會邊走邊唱。一對有情人終成眷屬,會不會如願以償?」
歌聲清脆宛轉,仿佛百靈鳥兒,那雙溫柔的眼波,更是始終凝注在夏潯的身上。歌聲唱罷,餘音裊裊,左右行進的軍士如雷的叫好聲還未停歇,另一個更加高亢清亮的聲音又唱了起來:「六十六條雪水,向着一起匯合,奔騰的塔里木河,滋潤着我的心窩……,你是否來將我探望,還是愛慕訴說衷腸,是否將那熄滅的火,重新點燃更燒旺……」
讓娜比西琳表現的更加熱情奔放,她唱歌時,那雙火辣辣的大眼睛一瞬不瞬地盯着夏潯,西域女子對表情的表達和追求熱烈而奔放,顯然沒有中原女子的那種含蓄內斂,以前兩人面對夏潯時的那種羞澀和畏怯,更多是地位上的巨大差距造成的。
這些天與夏潯朝夕相處,漸漸的,地位上的巨大鴻溝似乎差距不是那麼大了,一天天接近她們的故鄉,也喚醒了她們骨子裏的那種對愛的大方、熱烈的追求。
可惜,這亘古不變的原始景像在喚起她們思鄉之情的同時,也觸動了夏潯,他正抬頭看着那似乎壓得極低的雲頭,思緒隨着那宛轉的歌聲直上重宵,回到了他那遙遠的故鄉。他的故鄉,永遠也回不去了,在那裏時,從未覺